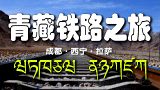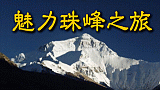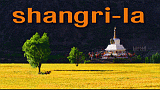介绍:约瑟夫·洛克 Joseph F.Rock
Filed Under 精彩网摘 By 美景旅游网
Posted on 本文最后更新于2006-11-05 15:13:40
From links http://www.mjjq.com/blog/archives/1416.html
 在20世纪2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洛克在中国的西南边疆拍摄了两万多张照片,这些变迁中的历史图景,现在大多已荡然无存,在保留中国西南自然生态的原始图像与边民的社会生活画面方面,这一成就后人根本就没机会去实现。
在20世纪2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洛克在中国的西南边疆拍摄了两万多张照片,这些变迁中的历史图景,现在大多已荡然无存,在保留中国西南自然生态的原始图像与边民的社会生活画面方面,这一成就后人根本就没机会去实现。
从四处流浪的植物学家到漏洞百出的地理学者
约瑟夫·洛克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1884年洛克生于维也纳一个仆人的家庭,他6岁丧母,13岁开始自学汉语,18岁开始在欧洲各地流浪,随后又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等地漂泊,1907年他到了夏威夷,在不到12年的时间里,自学成才的他从夏威夷森林与国土部门的一个植物采集员成为一个一流的植物学家,并在夏威夷大学任植物学教授。此外,这个怪才还精通匈牙利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和汉语等语言。
1922年2月洛克受美国农业部派遣,来中国云南寻找抗病毒的栗子树种。这是他渴望已久的第一次中国之行。自鸦片战争以后,动植物资源丰富的中国西南边疆便成为了西方探险家的“乐园”,英,法,俄等国的植物学家纷纷到这里来分一杯羹。洛克在这方面的“职业素养”自然也毫不逊色。当时美国农业部的大卫·费乐德告诉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洛克正巧在云南考察,《国家地理》杂志于是同意为1923年2月洛克在云南的探险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在《国家地理》杂志的资助下,在短短几个月内洛克就收集了60000件植物标本、1600件鸟类标本和60件哺乳动物标本。
但使洛克闻名遐迩的,还是他给《国家地理》写的那些文章。这些文章虽然都是洛克的“副产品”,但每篇稿酬高达1500美元。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基本的背景: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土匪滋扰层出不穷,贫困的边陲之地,土司与活佛的故事,一个奇特的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隔绝的世界。从洛克的行文来看,既动人心魄又虎头蛇尾,难怪《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对他的文章曾经大加指责:“缺少想象力,不能给人一个完整的印象,而且随心所欲,毫无章法,废话连篇,不知所云。”经常需要重新改写,作为一位装备一流的职业探险家,他缺乏最基本的地理测绘常识和训练,绘制的地图粗枝大叶。但这就是这位业余水平的地图绘制者,抗战时期曾为美国国防部地图署工作,为驼峰航线的开辟做出过巨大贡献。



洛克对山峰高度的测量曾屡屡漏洞百出,从来没有正确过一次,在1930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洛克声称位于青海的阿尼玛卿山高29661英尺,比珠穆朗玛峰还高,70年代我国的地理学家终于确立了阿尼玛卿山的高度只有6282米(20730英尺),比起珠峰的8848米(29198英尺)实在可称得上是个小弟弟。以至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的编辑再也不敢轻信洛克后来的那些“伟大的地理发现”,如1930年2月27日,他又给《国家地理》发电报,称“明雅贡嘎山为世界最高峰,高30250英尺”可是到1930年10月这个数字又缩了水,缩为25600英尺,但仍比实际高度高出许多,作为一个地理探险家,没有配备经纬仪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难怪有人说,洛克是用沸点温度计、无液气压计、测角器、棱镜罗盘和自己的想象来测量山峰高度的。
更让该杂志社深恶痛绝的是,1927年,洛克带两个纳西族助手到华盛顿学动物标本的制作,但洛克却屡屡干扰助手的学习,甚至带他们坐飞机在华盛顿的上空一览秋色。另一方面,洛克也常常对杂志社改变“他文章的意思”大发雷霆,双方的舌战从来没有间断过。
倒是该杂志社的助理编辑格雷夫斯说过一句公道话:“洛克是世界上最好的摄影师之一,是一位成果丰硕的探险家和地理学者,但同时也是一个最坏脾气的人。”1928年,洛克在木里的贡嘎岭为该杂志拍摄的彩色照片就有243张,黑白照片有503张,此外还采集了700件鸟类标本。1929年的贡嘎山之行他为美国农业部采集了317种植物,单是杜鹃花一项就有163种,共计30000件植物标本,1703件鸟类标本,为地理杂志摄制了900张彩色照片,1800张黑白照片,而且大部分的照片都是在条件艰苦的野外冲洗,特别是5乘7寸的彩色玻璃板。在20世纪2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洛克在中国的西南边疆拍摄了两万多张照片,这些变迁中的历史图景,现在大多已荡然无存,在保留中国西南自然生态的原始图像与边民的社会生活画面方面,这一成就后人根本就没机会去实现。
从自恋而虚荣的假“博士”到奢侈的探险家
洛克最大的成就也许还在于与当地的军阀和土司头人搞好关系,这是他一切探险活动的基本保障,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自称为“洛克博士”。有证据表明,为了取得大学的教职,他曾伪造过维也纳大学的学历,尽管从未取得过正式的学位、得到过荣誉学位的他对“博士”这个头衔是多么地洋洋自得。洛克在云南的地理探险完全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从时间上来说,他比金登·沃德和乔治·弗瑞斯特等植物学家和其他如法国的亨利·奥尔良等四方冒险家要晚,另外,从地域上来说,范围也主要限于滇西北,而英国的H·R·戴维斯少校在1894至1900年间曾四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考察,行程数千公里,对云南的地理与风土人情了如指掌。金登·沃德和戴维斯少校早在洛克之前就探访过木里,洛克明明知道这一点,但膨胀的虚荣心却忍不住为自己贴金,在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吉尔伯·特格多斯文的信中他曾自豪和避实就虚地写道,“没有一个白人在2月末月蚀时曾踏足过木里王国。”虚荣心很大程度上与他的白人至上主义有关,只要是白人没有去过的地方。阿尼玛卿山坐落在黄河上游的拐角处,顾影自怜的洛克在那里情不自禁地写道:“自创世以来,从没有白人站在这个地方”。这也许是那个时代所有西方地理与人文发现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这个有着优越感的白人却几乎无法与大多数白人朋友们和平共处,每次与白人朋友同行都是不欢而散。

图片: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 1884-1962)
在那时的云南,除了一条摇摇晃晃的滇越铁路外,自古以来惟一能在高原上畅通无阻的交通工具便是马帮,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洛克的马帮之旅为他们展现了一个神秘的领域。30年代曾与洛克一起在云南旅行过的埃德加·斯诺有过这样的感慨:“马帮,这是一个令人心醉的字眼,这蕴藏着神秘,蕴藏着不可知的推动力。”洛克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常常携带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这对于野外生活则显得过于奢侈,斯诺曾写道:“洛克习惯于野外生活,他有种种巧妙的设备,可以帮助一个孤寂的漫游者忘记却自己已经远离家室,远离亲人,远离美味佳肴。他有许多天才的发明,如折叠椅、折叠桌、折叠浴缸、热水瓶等等。无怪乎他所到之处,当地人敬畏之余无不把他看作一位外国的王爷。我本人能侧身于他的侍从之列也深感荣辛……这种生活确有一种乐趣,现在我才理解了洛克对这种生活的热爱,率领着自己的马帮,享受着一种特殊的激动人心的责任感,因为你对你的手下人和你自己的生命要负责任,日出之前的一个小时出发,在朦胧的朝雾中骑马前进,徒步爬山,爬得你四肢筋疲力尽,在日落时分到达一个从未见过的河谷,不知道晚上在什么样的房间铺床睡觉,别的什么也不指望,只想安安稳稳地睡上这好不容易才挣得的一觉。这些都是最简单最原始的需要,但满足这些需要后所得到的兴奋和激动,却是那些常年居住在城里,只和大马路打交道的人永远感受不到的”。
毫无疑问,洛克在云南的行走最初是以掠夺植物的商业目的为出发点的,当猎奇的目光扫过自然的风光和土著居民原始的生活状态时,他敏锐地认识到,这正是西方媒体所需要的“商业素材”,他挣到了钱,出了风头。而当他发现当地的民族文化所蕴藏的无穷魅力时,便请求《国家地理》杂志资助对纳西东巴文献的研究,但该杂志所关心的更多的只是读者的趣味和文章图片所带来的商业价值,而洛克的要求与这一切却背道而驰,于是断然拒绝了洛克的请求。此时,采集植物这项工作也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洛克与美国农业部、哈佛植物园的合作关系即不欢而散,这使洛克十分恨透了西方工业社会的冷酷与无情。尽管中国政局动荡,民不聊生,但与欧洲残酷的现代战争机器相比,洛克认为中国的土匪和军阀所进行的战争是业余水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遥远的云南仍算得上是和平的乐园。

图片:约瑟夫·洛克在雪山玉湖村的故居
30年代初,洛克已完全没有了收入的来源,然而却义无反顾地变卖所有家产,带上所有用来养老的积蓄回到他曾咒骂不已的中国西南边疆,从此,他与赖以谋生的植物学分道扬镳,全身心地投入对纳西文化的研究。30年代后,洛克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昆明,为寻找民族研究的相关资料,他一次又一次地外出旅行,漫游北京、上海、成都、南京等地,有时也回欧洲和美国。旅行是他的生活方式,有时这种生活方式的代价会变得不可思议,1936年2月3日,阳光明媚,洛克这天自己包租了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昆明号”从云南府飞到了丽江,在丽江停留几个小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为了在空中俯瞰高山和大地。抗日时期,洛克曾怂恿驼峰航线的美军飞行员带他穿越虎跳峡,并说虎跳峡只有12米宽,(现在的虎跳峡最狭窄的地方都有27至30米)并下命令低飞拍照,该飞行员后来回忆说,幸好当时刮起了大风没有低飞,不然洛克这家伙准会让他们送命。
从傲慢的白人中心主义者进化到孤独的文化相对论者
探险家的生活方式令他选择了独身,然而令他备感孤独的却是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没有人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这项工作使他耗尽心血,经济上陷于破产的边缘,年老多病的他常常感到绝望,洛克常常在日记写道:“今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30年代末,他时常想到自杀,为了防止自杀,他曾要求美国住昆明领事保罗·迈勒帮他保管手枪。斯诺说他是乐天精神与孤独性格的奇妙结合,在经历悲观与绝望后,他往往很快会恢复过来。
洛克深知,在社会文化激烈的变迁中,一些古老的传统文化正在消失,他的研究对保存这些东西至关重要,在研究纳西文化的过程中,孤独的洛克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947年《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在经历重重的劫难后终于出版,在该书的前言中,洛克深情地写道:“当我在这部书中描述纳西人的领域时,逝去的一切又一幕幕地重现在我的眼前,那么美丽的自然景观,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森林和鲜花,那些友好的部落,那些风雨跋涉的年月和那些伴随我走过漫漫旅途,结下深厚友谊的纳西朋友,都将永远铭记在我一生最幸福的回忆中”。
洛克十分同情西南的少数民族在旧社会所遭受的蹂躏和歧视,1949年,在丽江的洛克终于看到了:“红色政权解放了各民族的人民,并宣布他们具有与汉人同样的权利”。但是作为“帝国主义分子”的他则不得不离开中国,此时的他为研究纳西文化已经倾家荡产,晚年的他只有靠朋友们接济生活,为了能使专著出版,他不得不先后变卖最后的“财产”——数千卷东巴经书。洛克继继续续停留在中国的27年间,经他的手收集的有8000多本东巴经书,后来分别收藏在欧美的各大图书馆。解放后,流落在丽江民间的东巴经书作为封建迷信的毒草被焚烧殆尽,而那些美丽的森林也在60年代崛起的森工企业的电锯下一片片地消失。今天,当我们再来评判洛克的功过是非时,难免不留下丝丝苦涩回忆。
洛克所走过的文化之旅不但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的文化观,独来独往的他在临终前曾感叹到:“我曾经遭遇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困难。那时候到处都无和平可言,一个国家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另一个国家。我所经历的磨难和忧伤不胜枚举:“诸如土匪的骚扰,艰难的长途跋涉,战争年代,原子弹爆炸,通货膨胀,霍乱,以及载有我翻译纳西手稿的轮船被日本军舰击沉在印度洋”。与早年的白人中心主义不同,晚年的洛克反对把外来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任何一个民族,对于西方宗教在中国西南边疆的传播,洛克始终没有好感,他反对所有外来文化对这一区域的“污染”,这种观点有时甚至十分偏激和愤世嫉俗,洛克在《纳西人的生活与文化》里冷嘲热讽道:“在把纳西转变为信奉基督教方面,新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们都没有取得任何成功。没有纳西人愿意为外国传教士工作或参加他们的聚会。在丽江只有一个新教传教团,他属于圣灵基督教的变体。他们雇用四川的鸦片烟酒鬼作为助手,或雇用被西藏人半遗弃的懒惰的流浪汉。这些人一天之内就成了基督徒,过段时间又是喇嘛教信徒”。洛克又说:“纳西的生活娱乐很少,他们反对传教士干涉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及违反他们非常谦和的生活娱乐。他们被告诫不饮酒,不抽烟,也不跳舞。纳西是一个温良谦和的民族,具有比大多数白种人更高的道德标准。”
可以这么说,《消失的地平线》的作者希尔顿东方式的香格里拉幻景存在于西方文化的价值核心之中,在洛克看来:在美丽的自然风光中,土著文化才是真正的精髓,在遗作《纳西语英语百科全书》的序言中,他曾这样动情地写道:“我真正要感激的是那些纳西祭师,正是他们慢慢地打破了其隐匿的古老传统,耐心地开始教授我,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让我进入他们神圣的祭仪,进而揭开了存储在经书中的宗教内涵的珍贵价值。用这种文字,纳西人勾画出了他们的内部生活:自然界的力量激发着他们的情感,生与死的永恒主题,浪漫的爱情故事,他们对自然界的态度,自然哲理令人畏惧的力量使得他们与数不胜数的邪恶生灵搏斗——魔鬼、精灵、鬼怪,甚至是大小神灵。他们与神灵息息相通,并与激发出他们的想象力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从白人中心主义者进化到文化相对论者,这也许正是洛克与许多到过云南的外国人的不同之处。
这个西方人心灵的归宿是云南丽江,对于他来说,这不单是一个生活的恬静家园,同时也是他的精神家园,50年代他在夏威夷病重住院期间,此时的他已不可能回到中国,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会重返丽江完成我的工作……我宁愿死在那风景优美的山上也不愿孤独地呆在四面白壁的病房里等待上帝的召唤”。1962年12月5日,洛克终于在夏威夷走完了他孤独的人生之旅。在他活着的时候和逝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人类学方面的成就并未被美国人类学界的主流所接受,其专著也只有欧洲才得以出版,这个孤独者留下的只是一本又一本的专著,而在他的墓碑上只写着这样简单的几行字:
约瑟夫·F·洛克博士
植物学家——探险家
1884——1962
图片/资料来源:National Geographic 中国国家地理
相关链接:
照片:约瑟夫.洛克镜头下的稻城(1)
照片:约瑟夫.洛克镜头下的稻城(2)
照片:约瑟夫.洛克镜头下的稻城(3)
介绍:约瑟夫·洛克 Joseph F.Rock
约瑟夫·洛克的香格里拉发现之旅
图片:约瑟夫·洛克与神秘的木里王国
和为剑:破解香格里拉之谜
固定链接 | 归类:精彩网摘 | 发布于:2006-11-01 12:37:07
上一页:香格里拉不是“消失的地平线”
下一页:世界风光:尼泊尔-帕坦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