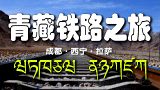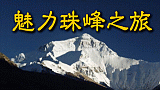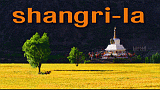[ 云南印象 ] 在世界最美的梅里雪山,心情象天一样蓝
Filed Under 旅行游记 By 旅行者
Posted on 本文最后更新于
From links http://www.mjjq.com/blog/archives/704.html
“我的出发包涵了我的结局”—T·S·艾略特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乐山乐水,仁智双见,陶醉在山水之间,吟咏成习,数千年来,风骚蔚然。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如果把自古以来歌颂山川的诗句编辑成册,必定是车载斗量,汗牛充栋。可是这些浩瀚的关于山和川的卷帙中,却绝少出现雪山与冰川。——实际上在我的印象里,只记得一句“窗含西岭千秋雪”,这“千秋雪”大概就是终年不化的雪山冰帽吧。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乐山乐水,仁智双见,陶醉在山水之间,吟咏成习,数千年来,风骚蔚然。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如果把自古以来歌颂山川的诗句编辑成册,必定是车载斗量,汗牛充栋。可是这些浩瀚的关于山和川的卷帙中,却绝少出现雪山与冰川。——实际上在我的印象里,只记得一句“窗含西岭千秋雪”,这“千秋雪”大概就是终年不化的雪山冰帽吧。
我想这是交通的原故,使古代书生们无缘与这些壮丽的风景邂逅。在中国,但凡出现雪山冰川的地方都道路险难、瘴疬弥漫,而古代的交通简陋、道路阻塞,更兼盗匪成群,偶尔出没于雪山高峡之间的人们多是为生活所迫甘冒生命危险的商队马帮,自然不会有文人。即使是朝廷要贬谪官员,那些迁客骚人,也极少被流放到滇藏地区的雪山脚下——那里实是被朝廷忽略的密境。就这样,雪山冰川,则成了被古诗词忽略了的壮丽景观。
面对蜀道之难,李白已“扪参历井仰太息”。而今我到达飞来寺,这天下午,站在路边,隔着澜沧江峡谷,遥遥望着天际的云——卷裹着梅里太子十三峰的浓云,心中充满忐忑。
梅里雪山,云南与西藏的界山,主峰卡瓦博格,海拨6740米。从高度上来说,中国多的是8000米以上的高峰,6000实在不算很起眼的高度。在西藏,许多雪山都是藏民的神山。卡瓦博格在藏民心目中的地位,却是比珠穆朗玛、冈仁波齐还要高的神圣雪山。每年的秋末冬初,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的大批香客不惜千里迢迢赶来朝拜。
目前世界上有14座8000米以上、几十座7000米以上的雪峰都被人类攀登者印上了足迹。而6000多米的卡瓦格博,至今还是处女峰。据我所知,自1902年开始,就不断地有欧洲的探险家试图登上卡瓦格博。直到1990年底,中日联合登山队带着当时最有经验的登山队员和最先进的登山设备,计划登顶这座神山,结果,1991年元月,在即将成功的前夜,突然发生了大雪崩,登山队在海拔5100米的3号营地与指挥部失去联系,十七名登山队员全部失踪,连个呼救信号都没有,而空军派出的搜救队只看到一片白茫茫的雪原,一点线索都没找到,别说活人,连死人都没找到。那次事件震惊世界!是当年的十大体育新闻之一。
直到七年以后,才有牧民在冰川末端发现了那次登山者的遗骸和遗物。
由那次山难,引发了“挑战自然极限”和“反对打扰人文崇拜”的争论,旷日持久,直到现在。雪山脚下的藏族群众是极力反对攀登他们敬仰的神圣雪山的,卡瓦博格峰是出现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中的神,与藏族的大神莲花生大师极有渊源。按雪山脚下藏民的说法:那次登山,之前顺利,后来发生灾难的原因,是卡瓦博格山神正好去参加山神大会了,回来时发现有几个人类在它的肩膀上,它就抖了抖身子,把他们拂了下来。
实际上由于垂直气候明显,梅里的天气变幻无常,雪雨阴晴全在瞬息之间,而以梅里雪山为玫瑰结*的几条冰川属于低海拔海洋性冰川,本来就极不稳定,有科学家根据那次山难发生地与遗物发现地的距离和时间,计算出明永冰川的流速是每年530米,为中国冰川运动速度之最。雪山险而神秘,实是跟海拔和纬度有关。
(*呵呵"玫瑰结"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学来的冰川地质学名词,大意是指冰川发源地的主要山峰。以后提到的"冰碛物""侧碛陇"什么的也是《中国国家地理》上看来的^o^)
我是反对“征服”“挑战”之类的说法,征服是个暴力词汇,是强权意志;而挑战,人类唯一有资格挑战的是每一位人类自己,决不应该是大自然。但我也崇敬登山者、探险家,甚至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造物之神设置的险境绝景,有时只接纳挑战自我成功者的觐见。当然,有时还要运气。每一个站在顶峰或者到达奇境的人,都应该感谢大自然,感谢它的容许。
这次旅行的目的是来仰望卡瓦博格的,怀着朝觐的态度。但它给我的神秘,竟使见它一面如此不易。此时雪山方向的天边,云雾缭绕,青黛的远山坡上偶尔露出一小片冰舌,不一会儿又隐入云中。仅夜里10点多钟,雪山才在墨蓝墨蓝的苍穹远方隐隐卓卓地现身。我在屋外站了一会儿,山风如冰箭,射透秋衣。
第二天我凌晨五点即起,守在观景台。飞来寺观景台在雪山的东面,若天气好,太阳从东边升起,朝霞则印上雪山,此时的几分钟内,整个梅里雪山就成了金色的了,这就是所谓的“日照金山”。但这更是不能常见的奇景,梅里的天气,一天之内,随时雨雪晴云,现代气象学,至今难以预报。有些色(摄)迷,为了一睹“日照金山”的壮丽,不惜在飞来寺住上十天半个月。
可是我只有一个早晨的时间,我实在没有什么资格埋怨天气,只怪我羁绊太多,虔诚未够。别说日照金山,连我梦寐以观的雪山,也是只见了个影子。恋恋不舍地守了三个小时,看到了一小片朝霞,印在山腰上,转瞬间就被云雾掩了,没一会儿,更多的云,由谷底生升,连观景台上的我们,也被掩了。
下面的行程是明永冰川观景台。向导安慰我说梅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不定一会儿天气就好了,在明永冰川观景台,也能看到卡瓦博格。
我们的车,跨过澜沧江,沿着条简易公路,向深山更深处颠簸而去,到公路的终点,向导说还有十五里,“之”字形上山的羊肠小道,可以雇骡马。估计两个小时能到观景台。
我决定徒步,既是来朝觐的,这一路也太轻松了。我们的队伍中,只有那位小军官愿意和我一起徒步上山,他说他们集训行军也是经常的——果然,后来的行程中,他把我落得远远的,甚至比骡子还快。实际上,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在走。
我和小军官先行一步,刚开始坡路缓些我能还耽于风景,停下来拍拍照,看看远山,小军官已经走远了,想要追上去,才发现高原空气稀薄,呼吸越来越重,路却越来越陡,仿佛永无止境的上坡呀上坡。以至于后来恨不得要把肺凿上几个窟窿才喘得过来。体能到达极限的那段时间,我已经不能左右我的躯体,仅凭意志在数数,鼓励自己坚持走完一百步,再一屁股坐下,气喘如牛,汗水从头发滴入尘土,咬着牙爬起来继续去数下一段一百步的时候,我觉得找到一件事情去坚持,并且想到这个坚持肯定会成功时,就快乐起来,想唱歌,肺却不同意。
我本来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左脚,一个月前,我的左脚脚踝严重扭伤,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现在根本没好利落。上山时把重心尽量放在右脚跟,结果后来右脚脚踵磨起了水泡,并且破了。这下好,左脚隐隐地痛,右脚生生地痛,不知是我姿势不对还是鞋子的问题,不过幸好还能坚持得住。路是由碎石、尘土和骡粪铺成的,森林茂密,冰川溶水汇成的溪流就在不远处喧响。我们的骡队很快就追上了我,朋友们跟我聊两句,鼓励我。但跟着骡队走很受罪,大口喘气吸入了不少骡子踏起尘土,混着浓烈的骡粪气味。
每只骡子都有个骡夫,藏族,本地山民,皮肤黝黑,脸颊上两块标志性的高原红。有男有女,赶着自家的骡子,一边喘气,一边却还能有说有笑地聊天,有位十来岁的小姑娘,和我一样喘得说不出话来,行至坡陡处,拉着自家骡子的尾巴上行,倒也一步没落下。我却不行了,捂着鼻子让骡队先行,被骡粪尘土弄得灰头灰脸。他们在前面拐过一个弯,看不见了,却听见清脆嘹亮的山歌传来。不断有别的骡队超过我,骡背上的年青人看到我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兴高采烈地说话,怀里抱着轻装氧气瓶,熟人般冲我微笑点头,或许是羡慕或许是鼓舞。
体能极限一过,呼吸渐渐匀称,行走也轻松多了。半途中遇到另一位独自背包徒步的女孩,同行一程,互相鼓励,得知她也是来自北京,跟着同伴掉队了,她倒也不算太急,只是不断地问:还要走多久啊。休息的时候,她看中树杆上一只巨大的灵芝形菌类,一心想把它弄下来玩,结果胳膊被野蜂蛰了一口,幸好没什么大碍,苦着脸,看见一只松鼠,又高兴起来。
冰川溶水化成的溪流深成山涧,越往上行,水势越小,透过山边的灌木,能看到冰舌末端了,但没有看到冰川冰舌由于夏季收缩而形成的冰碛陇。随树木的疏密,冰川或隐或现,渐渐看清是一条冰雪大河,挟裹着灰黑的冰碛物,从云端奔腾而下,波浪翻滚却是静止的。又走进了一片树林,突然似乎听到隐隐的雷声,刚开始以为是错觉,却又来了一声,轰隆隆比刚才更清晰,山谷中传来回音。可是此时天空白云朵朵,或见蓝天。与北京女孩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雪崩”!
我们想跑到视野开阔的路段去看雪崩,可是奋力跑了不到十步,就发现双腿就象是岩石,根本就不是自己所能主宰的。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我们一前一后,象两条筋疲力尽的鱼,张嘴瞪眼,大口大口地喘。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听着轰隆隆的声音渐渐消失。
此时已没有了山路,骡马的终点到了,游客们全部在此下鞍。沿着冰川剥蚀的岩壁,人们修了一条栈道。继续上行,栈道比山路好走多了,视野也开阔。栏杆上挂满了经幡,明永冰川就在栈道下面,高大的雪峰仍在云里,冰川对面的几座山峰略矮,未入雪线,从云中现身,指向苍天,数峰之间,另一条冰川的冰舌悬挂在山崖之上,化成溪水,如一条白线,细细弯弯,长长地垂下,没入明永冰川冰雪表层的下面。
在最高的观景台,我和北京女孩各自找到了同伴。我的朋友中有给我计时的,说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正合向导预计的时间。这里的视野更好,心胸也随之开阔,深呼吸,却不是为了喘气。张开双臂,想像飞翔的可能。人们到了这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做扩胸运动,大声喊叫。谷底的明永冰川浩浩荡荡,挟裹着冰碛物,静静地剥蚀山体。越往上越白,冰川的上游,白茫茫分不清是冰雪还是浓云。这时又发生雪崩了,只是规模小些,从一块岩石上跃下一些冰雪,冰川的断面呈蓝色。
心情也是蓝色的,甚至天空也渐渐蓝起来,云慢慢散去,可是缠绵着雪山的云,却依然那么浓。在同伴的催促下,不得不离开了。Let is be. Let is be.
下山快多了,脚后跟受力小了,大步流星,踏起尘土飞扬。回程不能不说是带了些遗憾的,大家坐在车里,或许也是爬山累了,都不说话。我照旧一个人塞上耳机蜷在后排座椅贴着车窗,随一首老歌,那些遗憾扩大成惆怅。我们的车弯弯曲曲盘在峡谷里,阑沧江水湍急且浑浊,这里群山贫瘠,不怎么生长树木。我们的车挂着低档轰轰地开始爬坡,折弯,再折弯。有的同伴已昏昏欲睡。
梅里地区的天气果然变幻万端,此时天蓝云白,只是阳光被山遮住,没照进峡谷。我仍未死心,朝雪山方向望去,视线却也被那几座矮山挡住。上升,又一个折弯,突然开出了山影,阳光哗地涌进车窗,明晃晃白花花淹没了整个视觉。眯着眼睛,手打凉棚——
呀!呀!天上一座银色的金字塔,重重地撞击我的额头。刹那间,仿佛一生中所有的狂喜和巨痛全部同时涌现,那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幸福与悲怆不管不顾地相互拥抱着,上升。上升。眩晕中,我甚至有些哽咽,牙齿微微打战,泪水濡湿睫毛。
卡瓦博格。卡瓦博格神山。——玉砌银雕,祥云环绕,万峰朝宗。我彻底明白了藏民们为何如此崇拜它;我终于知道洛克为什么说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雪山”了;我完全相信《消失的地平线》就是以它为原型才能描绘出卡尔波尔雪山。
嗯,这才是令我满意的开头,好了,我就用这个开头结束这次旅行吧:云南往西,偏北!
面对蜀道之难,李白已“扪参历井仰太息”。而今我到达飞来寺,这天下午,站在路边,隔着澜沧江峡谷,遥遥望着天际的云——卷裹着梅里太子十三峰的浓云,心中充满忐忑。
梅里雪山,云南与西藏的界山,主峰卡瓦博格,海拨6740米。从高度上来说,中国多的是8000米以上的高峰,6000实在不算很起眼的高度。在西藏,许多雪山都是藏民的神山。卡瓦博格在藏民心目中的地位,却是比珠穆朗玛、冈仁波齐还要高的神圣雪山。每年的秋末冬初,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的大批香客不惜千里迢迢赶来朝拜。
目前世界上有14座8000米以上、几十座7000米以上的雪峰都被人类攀登者印上了足迹。而6000多米的卡瓦格博,至今还是处女峰。据我所知,自1902年开始,就不断地有欧洲的探险家试图登上卡瓦格博。直到1990年底,中日联合登山队带着当时最有经验的登山队员和最先进的登山设备,计划登顶这座神山,结果,1991年元月,在即将成功的前夜,突然发生了大雪崩,登山队在海拔5100米的3号营地与指挥部失去联系,十七名登山队员全部失踪,连个呼救信号都没有,而空军派出的搜救队只看到一片白茫茫的雪原,一点线索都没找到,别说活人,连死人都没找到。那次事件震惊世界!是当年的十大体育新闻之一。
直到七年以后,才有牧民在冰川末端发现了那次登山者的遗骸和遗物。
由那次山难,引发了“挑战自然极限”和“反对打扰人文崇拜”的争论,旷日持久,直到现在。雪山脚下的藏族群众是极力反对攀登他们敬仰的神圣雪山的,卡瓦博格峰是出现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中的神,与藏族的大神莲花生大师极有渊源。按雪山脚下藏民的说法:那次登山,之前顺利,后来发生灾难的原因,是卡瓦博格山神正好去参加山神大会了,回来时发现有几个人类在它的肩膀上,它就抖了抖身子,把他们拂了下来。
实际上由于垂直气候明显,梅里的天气变幻无常,雪雨阴晴全在瞬息之间,而以梅里雪山为玫瑰结*的几条冰川属于低海拔海洋性冰川,本来就极不稳定,有科学家根据那次山难发生地与遗物发现地的距离和时间,计算出明永冰川的流速是每年530米,为中国冰川运动速度之最。雪山险而神秘,实是跟海拔和纬度有关。
(*呵呵"玫瑰结"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学来的冰川地质学名词,大意是指冰川发源地的主要山峰。以后提到的"冰碛物""侧碛陇"什么的也是《中国国家地理》上看来的^o^)
我是反对“征服”“挑战”之类的说法,征服是个暴力词汇,是强权意志;而挑战,人类唯一有资格挑战的是每一位人类自己,决不应该是大自然。但我也崇敬登山者、探险家,甚至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造物之神设置的险境绝景,有时只接纳挑战自我成功者的觐见。当然,有时还要运气。每一个站在顶峰或者到达奇境的人,都应该感谢大自然,感谢它的容许。
这次旅行的目的是来仰望卡瓦博格的,怀着朝觐的态度。但它给我的神秘,竟使见它一面如此不易。此时雪山方向的天边,云雾缭绕,青黛的远山坡上偶尔露出一小片冰舌,不一会儿又隐入云中。仅夜里10点多钟,雪山才在墨蓝墨蓝的苍穹远方隐隐卓卓地现身。我在屋外站了一会儿,山风如冰箭,射透秋衣。
第二天我凌晨五点即起,守在观景台。飞来寺观景台在雪山的东面,若天气好,太阳从东边升起,朝霞则印上雪山,此时的几分钟内,整个梅里雪山就成了金色的了,这就是所谓的“日照金山”。但这更是不能常见的奇景,梅里的天气,一天之内,随时雨雪晴云,现代气象学,至今难以预报。有些色(摄)迷,为了一睹“日照金山”的壮丽,不惜在飞来寺住上十天半个月。
可是我只有一个早晨的时间,我实在没有什么资格埋怨天气,只怪我羁绊太多,虔诚未够。别说日照金山,连我梦寐以观的雪山,也是只见了个影子。恋恋不舍地守了三个小时,看到了一小片朝霞,印在山腰上,转瞬间就被云雾掩了,没一会儿,更多的云,由谷底生升,连观景台上的我们,也被掩了。
下面的行程是明永冰川观景台。向导安慰我说梅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不定一会儿天气就好了,在明永冰川观景台,也能看到卡瓦博格。
我们的车,跨过澜沧江,沿着条简易公路,向深山更深处颠簸而去,到公路的终点,向导说还有十五里,“之”字形上山的羊肠小道,可以雇骡马。估计两个小时能到观景台。
我决定徒步,既是来朝觐的,这一路也太轻松了。我们的队伍中,只有那位小军官愿意和我一起徒步上山,他说他们集训行军也是经常的——果然,后来的行程中,他把我落得远远的,甚至比骡子还快。实际上,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在走。
我和小军官先行一步,刚开始坡路缓些我能还耽于风景,停下来拍拍照,看看远山,小军官已经走远了,想要追上去,才发现高原空气稀薄,呼吸越来越重,路却越来越陡,仿佛永无止境的上坡呀上坡。以至于后来恨不得要把肺凿上几个窟窿才喘得过来。体能到达极限的那段时间,我已经不能左右我的躯体,仅凭意志在数数,鼓励自己坚持走完一百步,再一屁股坐下,气喘如牛,汗水从头发滴入尘土,咬着牙爬起来继续去数下一段一百步的时候,我觉得找到一件事情去坚持,并且想到这个坚持肯定会成功时,就快乐起来,想唱歌,肺却不同意。
我本来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左脚,一个月前,我的左脚脚踝严重扭伤,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现在根本没好利落。上山时把重心尽量放在右脚跟,结果后来右脚脚踵磨起了水泡,并且破了。这下好,左脚隐隐地痛,右脚生生地痛,不知是我姿势不对还是鞋子的问题,不过幸好还能坚持得住。路是由碎石、尘土和骡粪铺成的,森林茂密,冰川溶水汇成的溪流就在不远处喧响。我们的骡队很快就追上了我,朋友们跟我聊两句,鼓励我。但跟着骡队走很受罪,大口喘气吸入了不少骡子踏起尘土,混着浓烈的骡粪气味。
每只骡子都有个骡夫,藏族,本地山民,皮肤黝黑,脸颊上两块标志性的高原红。有男有女,赶着自家的骡子,一边喘气,一边却还能有说有笑地聊天,有位十来岁的小姑娘,和我一样喘得说不出话来,行至坡陡处,拉着自家骡子的尾巴上行,倒也一步没落下。我却不行了,捂着鼻子让骡队先行,被骡粪尘土弄得灰头灰脸。他们在前面拐过一个弯,看不见了,却听见清脆嘹亮的山歌传来。不断有别的骡队超过我,骡背上的年青人看到我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兴高采烈地说话,怀里抱着轻装氧气瓶,熟人般冲我微笑点头,或许是羡慕或许是鼓舞。
体能极限一过,呼吸渐渐匀称,行走也轻松多了。半途中遇到另一位独自背包徒步的女孩,同行一程,互相鼓励,得知她也是来自北京,跟着同伴掉队了,她倒也不算太急,只是不断地问:还要走多久啊。休息的时候,她看中树杆上一只巨大的灵芝形菌类,一心想把它弄下来玩,结果胳膊被野蜂蛰了一口,幸好没什么大碍,苦着脸,看见一只松鼠,又高兴起来。
冰川溶水化成的溪流深成山涧,越往上行,水势越小,透过山边的灌木,能看到冰舌末端了,但没有看到冰川冰舌由于夏季收缩而形成的冰碛陇。随树木的疏密,冰川或隐或现,渐渐看清是一条冰雪大河,挟裹着灰黑的冰碛物,从云端奔腾而下,波浪翻滚却是静止的。又走进了一片树林,突然似乎听到隐隐的雷声,刚开始以为是错觉,却又来了一声,轰隆隆比刚才更清晰,山谷中传来回音。可是此时天空白云朵朵,或见蓝天。与北京女孩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雪崩”!
我们想跑到视野开阔的路段去看雪崩,可是奋力跑了不到十步,就发现双腿就象是岩石,根本就不是自己所能主宰的。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我们一前一后,象两条筋疲力尽的鱼,张嘴瞪眼,大口大口地喘。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听着轰隆隆的声音渐渐消失。
此时已没有了山路,骡马的终点到了,游客们全部在此下鞍。沿着冰川剥蚀的岩壁,人们修了一条栈道。继续上行,栈道比山路好走多了,视野也开阔。栏杆上挂满了经幡,明永冰川就在栈道下面,高大的雪峰仍在云里,冰川对面的几座山峰略矮,未入雪线,从云中现身,指向苍天,数峰之间,另一条冰川的冰舌悬挂在山崖之上,化成溪水,如一条白线,细细弯弯,长长地垂下,没入明永冰川冰雪表层的下面。
在最高的观景台,我和北京女孩各自找到了同伴。我的朋友中有给我计时的,说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正合向导预计的时间。这里的视野更好,心胸也随之开阔,深呼吸,却不是为了喘气。张开双臂,想像飞翔的可能。人们到了这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做扩胸运动,大声喊叫。谷底的明永冰川浩浩荡荡,挟裹着冰碛物,静静地剥蚀山体。越往上越白,冰川的上游,白茫茫分不清是冰雪还是浓云。这时又发生雪崩了,只是规模小些,从一块岩石上跃下一些冰雪,冰川的断面呈蓝色。
心情也是蓝色的,甚至天空也渐渐蓝起来,云慢慢散去,可是缠绵着雪山的云,却依然那么浓。在同伴的催促下,不得不离开了。Let is be. Let is be.
下山快多了,脚后跟受力小了,大步流星,踏起尘土飞扬。回程不能不说是带了些遗憾的,大家坐在车里,或许也是爬山累了,都不说话。我照旧一个人塞上耳机蜷在后排座椅贴着车窗,随一首老歌,那些遗憾扩大成惆怅。我们的车弯弯曲曲盘在峡谷里,阑沧江水湍急且浑浊,这里群山贫瘠,不怎么生长树木。我们的车挂着低档轰轰地开始爬坡,折弯,再折弯。有的同伴已昏昏欲睡。
梅里地区的天气果然变幻万端,此时天蓝云白,只是阳光被山遮住,没照进峡谷。我仍未死心,朝雪山方向望去,视线却也被那几座矮山挡住。上升,又一个折弯,突然开出了山影,阳光哗地涌进车窗,明晃晃白花花淹没了整个视觉。眯着眼睛,手打凉棚——
呀!呀!天上一座银色的金字塔,重重地撞击我的额头。刹那间,仿佛一生中所有的狂喜和巨痛全部同时涌现,那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幸福与悲怆不管不顾地相互拥抱着,上升。上升。眩晕中,我甚至有些哽咽,牙齿微微打战,泪水濡湿睫毛。
卡瓦博格。卡瓦博格神山。——玉砌银雕,祥云环绕,万峰朝宗。我彻底明白了藏民们为何如此崇拜它;我终于知道洛克为什么说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雪山”了;我完全相信《消失的地平线》就是以它为原型才能描绘出卡尔波尔雪山。
嗯,这才是令我满意的开头,好了,我就用这个开头结束这次旅行吧:云南往西,偏北!
固定链接 | 归类:旅行游记 | 发布于:2006-01-10 22:37:47
上一页:[ 云南印象 ] 大理游:造作的人,美不胜收的苍山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