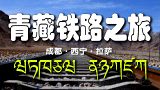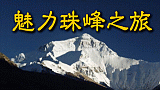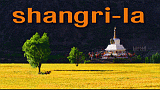[ 发现之旅 ] 华夏第一都 - 撒落人间的神秘王都
Filed Under 精彩网摘 By 旅行者
Posted on 本文最后更新于
From links http://www.mjjq.com/blog/archives/840.html

被二里头“烤”了6年
清晨,太阳还没有露出地平线,四周仍然静悄悄的,不时能听到远处传来清脆的鸡啼声。我草草吃了一点简单的干粮,便走出考古队的大院,来到了通往二里头遗址的乡间小路上。在田间,早起的村民已经忙碌起来,大片大片绿油油的麦子正在转黄,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年的到来。不远处,薄雾笼罩的村庄上空升起了袅袅炊烟,飘向了村外起伏的山峦。
就在这儿的一片麦地里,二里头遗址不动声色地潜伏着,像一条酣睡的巨龙,一旦醒来必将震惊世界。如果没有人特别指出,谁都不会相信,这里就是“华夏第一都”,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而且,经过几代考古学者几十年的潜心研究,这里众多的发现,足以让任何对考古界一无所知的门外汉都会怦然心动。
在近4000年前,这里曾经出现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宫殿建筑,宫殿四周有整齐宽阔的大道,周围生活着两万多名的居民,其规模足以傲视整个东亚地区。然而,经过3000多年的风雨飘摇之后,二里头却最终化成了掩埋地下的一抔黄土。如果没有后来的发掘,祖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不会相信,他们的脚下竟然埋着一座震惊世界的王朝都城。
我的工作就是寻找这座都城遗存下来的蛛丝马迹,让它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我眼里,它是上天无意中撒落人间的神秘王都,任何考古工作者梦寐以求的绝佳研究平台。
二里头遗址位于今河南偃师境内的洛阳盆地中,为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区。盆地内是广袤的平原,自古被认为是“天下之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二里头遗址就坐落于洛阳盆地东部、古伊洛河北岸的台地上,其西距汉魏洛阳故城约5公里,距隋唐洛阳城约17公里,其东北6公里处是偃师商城。遗址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前临伊洛,后据黄河,地理形势十分优越。

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发掘工作持续已有40余年。遗址丰富的内涵不断给世人带来惊喜,有众多的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
近年,在这块热土上,我们又发掘出几个“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车辙痕迹、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堪称“超级国宝”的早期龙形象珍品——大型绿松石龙形器。
这一距今3000余年、兴盛了约300年的都城遗址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以其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核心文化”。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应是夏王朝最后的都城,由于尚未发现当时的文字,这一问题仍是待解之谜。
1999年,我接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那年恰好是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发掘40周年。我是第三任队长,也是第三代队长。前辈们的辛勤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奠定了深入探索的良好基础。但如何站在前人肩膀上更上一层楼,是摆在我们面前极艰巨的任务。当时,我有一种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被无数关注的目光“烤”着的感觉。
这一“烤”就是6年,而且愈陷愈深……
发现最高等级的贵族墓
2002年4月,田野里的小麦长势喜人。微风一过,绿油油的麦浪起伏不定,摇曳生姿,而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发掘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这些天,我心中隐隐有一个预感:最近会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面世。果然,一天上午,年轻队友李志鹏走到我身旁,压低了声音说:“许老师,出铜器了!”我赶忙和他来到他负责的探方处。这个探方中有一座很大的二里冈上层时期的灰坑,灰坑打破了2号和4号建筑基址之间的路土和垫土,并穿透了其下叠压着的3号建筑南院中的路土。灰坑已基本清毕,刚才李志鹏在刮灰坑的坑壁剖面时,发现有铜器露头,随即用土盖好后向我报告。
我们仔细剥去表面的覆土,一件饰有凸弦纹的铜铃的一角露了出来。阳光下,青铜所特有的绿锈惹人心动,近旁还有人骨暴露。这应是一座身份较高的贵族墓。被灰坑破坏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我马上让他盖好,先扩大发掘面积,寻找墓葬范围,确认其开口层位。

经仔细观察,墓葬开口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建筑——3号基址南院的路土层之间,说明墓葬系该建筑使用期间埋设的。因此,我们在墓葬正式清理前,已可确认其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第二期)。自1959年首次发掘以来的40余年间,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的第二期墓葬仅发现过1座。而且,根据以往经验,出土铜铃的墓一般会伴有嵌绿松石铜牌饰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玉、漆、陶礼器。在这座墓发现前后,我们在该墓所在的3号建筑基址的南院和中院发现了建筑使用时期埋设的数座贵族墓,这些墓葬成排分布,间距相近,方向基本相同。尽管多遭破坏,这些墓葬还是出土了不少随葬品。这是二里头遗址发掘40余年来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成组贵族墓。成组高规格贵族墓埋葬于宫殿院内的现象,对研究这一建筑的性质和二里头文化的葬俗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3号墓又是这些墓葬中最接近3号建筑基址中轴线的一座,它的规格很可能高于以往在宫殿区周围甚至它近旁发现的同类墓。
3号墓葬为近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的方向接近正南北向。在揭开墓葬上面所叠压的路土层后,我们得知这座墓的长度超过2.2米,宽度达1.1米以上,残存深度为半米余。不要小看了这墓的规模,虽然与后世的达官显贵的墓葬相比,它小得可怜,但在二里头时代,它可是属于迄今已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墓(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王一级的墓葬)。这座墓让我们充满了期待。
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大灰坑打破了墓的西南部。墓主人侧身直肢,头朝北,面向东,部分肢骨被毁。后来经体质人类学家鉴定,墓主人是一名成年男子,年龄在30~35岁之间。墓底散见有零星的朱砂(这种红色矿物质是二里头贵族墓中的常见之物,一般认为应与宗教信仰有关,同时是身份等级的标志物),没有发现明确的棺木痕迹。

墓内出土随葬品相当丰富,包括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白陶器、漆器、陶器和海贝等,总数达上百件。玉器和海贝这类远隔数千里以外的珍罕品出现于贵族墓中,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
发现3号墓的当晚,我们即开始对墓葬进行“一级守护”。当时我手下有3名年轻队友、4名技工,以及来队实习的9名学生,可谓兵强马壮。我们安排“两班倒”,上半夜一拨,包括女生,下半夜则全为男性。我们又从邻近的圪垱头村借来一条大狼狗,还把我们的“大屁股”北京吉普2020开去,车头对着黑黢黢的墓穴,隔一会儿用车灯扫一下。
上半夜感觉还比较“浪漫”,大家说说笑笑,数着星星,贪婪地嗅着晚春旷野上散发着麦香的空气。有的男生还不时吼上一两句粗犷的民谣。下半夜则遭了罪,4月中旬的夜晚,昼夜温差很大,寒意袭人。
后来大家戏称这是为二里头贵族“守夜”。
神秘的大型绿松石器
随即,我们紧张而有序地清理着3号墓室。在墓主人的骨骼显露之前,已经有一些靠上的器物开始露头,其中包括细小的绿松石片。我们对绿松石片的出土并不惊奇,根据以往经验,它应该是嵌绿松石牌饰的组件。但随着揭露面积的扩大,我们开始意识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发现。
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70厘米。要知道,迄今为止,镶嵌牌饰仅1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长度都在15厘米左右,最大的一件异形器的长度也只有20余厘米,而且一般都有铜质背托。3号墓的绿松石片则分布面积大,且没有铜质背托。墓主人肩部一带的绿松石片位置较高,较为零星散乱,我们推测系棺木腐朽塌落时崩溅而致,因而对其保存状况并不乐观。位于墓主人腰部附近以及胯部一带的绿松石片则保存较好,有些还能看出由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拼合而成的图案。这颇令我们激动,以往在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都应是黏嵌于木、皮革或织物等有机物上,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散乱的原因,除了棺木朽坏时为墓葬填土压塌外,也不排除清理者缺乏整器概念或清理经验。
因此,3号墓的这一发现弥足珍贵。但绿松石片极为细小,每片的大小仅有数毫米,厚度仅1毫米左右。这使得清理极为困难,稍不留意,甚至用嘴吹去其上的土屑都可能使绿松石片移位。而一旦有大面积的移位,则以后不可能对原器进行复原。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清理得越细越不利于今后的保护和复原。于是紧急向社科院考古所李存信技师求援。李存信建议,即便他们赶赴现场,因条件限制,也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好地揭取出来,最好是先整体起出,运回室内,再按部就班地清理。

于是,我们停止对大型绿松石器的细部清理,在平面图上标示出已知的大致轮廓,准备好木板、绳子、钢丝、石膏等物品,准备整体起取绿松石器。
按照田野操作规程获取了墓葬的基本数据后,我们开始整体起取大型绿松石器。当然,最为理想的是将整座墓全部起取,但依当时发掘现场的条件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把墓主人颈部的海贝串饰也纳入了整体起取的范围,即从墓主人的下颌部(头骨在发掘前已被压塌)取至骨盆部。好在墓以下即为生土(未经人类活动扰动过的土),将下部和周围掏空,塞以木板,周围套上已钉好的木框,再在木框与土之间填以石膏浆,上部精心加膜封盖。然后用钢丝捆好木箱。这一长1米多、宽近1米的大箱,由6个小伙子吃力地抬上了吉普车,送回位于二里头村内考古队的住地。
到了住地,放在哪儿又成了问题。因为木箱内还有铜铃,恐怕会成为窃贼的目标。抬到二楼太困难,而一楼除了我的卧室兼办公室、值班室外,都无人住。于是有技工建议:“队长,还是先放到你屋里吧!”也只好这样了。20余年的考古生涯,我已不介意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数千年前的死者“亲密接触”。就这样,这个二里头贵族与盖在他身上的那条绿松石龙与我“同居”了一个多月,直到它被运到北京。
“超级国宝”碧龙游出水面
由于北京的清理条件比我们队里好得多,我决定把大木箱运回北京。我们的吉普车费尽周折,才把大木箱安全送到了北京。
经过近两年的等待,到2004年夏天,专家李存信开始揭开箱盖进行清理。从小心翼翼地剔凿去石膏,一直到总体轮廓出来,颇为不易。当看到我们为之付出艰辛努力的这件宝贝,居然是一条保存相当完好的大龙,顿感此前一切丰富的想象与推断都变得黯然失色。当你从上面俯视这条龙时,感觉它分明正在游动;当你贴近它硕大的头与其对视时,它那嵌以白玉的双眼也在瞪着你,仿佛催你读出它的身份。就这样,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逐渐“游出水面”。
这件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的身上,由肩部至髋骨处,与骨架相比略有倾斜,头朝西北,尾向东南。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原应黏嵌在木、革之类有机物上,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仅在局部发现白色灰痕。全器整体保存较好,图案清晰可辨,仅局部石片有所松动甚至散乱。由铜铃在龙身之上这一现象看,可以排除龙形器置于棺板上的可能。又据以往的发现,铜铃一般位于墓主人腰际,有学者推测应置于手边甚或系于腕上,联系到墓主人侧身,而绿松石器与其骨架相比上部又略向外倾斜,这件龙形器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而呈拥揽状。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色彩绚丽。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置于由绿松石片黏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绿松石拼合出有层次的图案,多处有由龙头伸出的弧线,似表现龙须或鬓的形象,另有拼嵌出圆孔的弧形纹样。
这一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龙头部为何有一个略呈矩形的托座?托座上的图案究竟表现了什么含意?从绿松石龙头部清理出来后,我就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一日,我凭印象查找曾看过的一件出土于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陶器盖上的刻画兽面纹。再次看到这一兽面纹,我不禁连连感叹其与绿松石龙头太像了。你看那面部的轮廓线、梭形眼、蒜头鼻子,甚至连鼻梁都是相同的三节,简直如出一辙。最具启发性的是从新砦兽面伸出的卷曲的须鬓,让我们茅塞顿开。托座上那一条条由龙头伸出的凹下的弧线,展现的不正是用绿松石难以表现的龙须或龙鬓的形象吗?
新砦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之间的相似性,还有更深一层意义。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由中原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演进的过渡期文化,可以看做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当然这一认识主要是来源于以陶器为主的文化因素的比较。而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表现手法的高度一致,则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上彰显了二者密切的亲缘关系。也可以说给绿松石龙找到了最直接的渊源与祖型。
至于以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或稍晚的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图案,则大部分应是绿松石龙尤其是其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因此,绿松石龙又成为解读嵌绿松石铜牌饰这一国之瑰宝的一把钥匙。
由于3号墓位于宫殿区内,最接近所在建筑的中轴线,且出土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其墓主人身份也要远高于随葬铜牌饰的墓主人。绿松石龙形器或嵌绿松石铜牌饰都与铜铃共出,随葬这两种重要器物的贵族,其身份是否与其他贵族有异?如是,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是乘龙驾云、可以通天彻地的巫师吗?
龙是中华民族神圣的图腾,并不专属于某一族系。因此,尽管文献上有不少夏人与龙关系密切的记载,但它们的出土还是无法确证二里头文化肯定就是夏文化。
“军令状”引发的新发现
无论古今中外,道路都是城市的骨架和动脉,且常常具有区划功能。鉴于此,考古学家往往以道路为切入点来探究城市遗址的布局框架。在对二里头都邑布局的探索中,我们也深切地意识到中心区主干道的意义,因此对主干道的探寻就成为田野工作的重中之重。
根据勘探记录,我队在1976年钻探发现2号宫殿基址的同时,在其东侧钻探出一条南北向大路,当时已追探出200余米,因冬季麦田浇水而中止。20余年后,当我在二里头考古队捧读已经发黄的记录和图纸中的这一线索时,兴奋之情难以抑制。我预感到这条大路是揭开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
2001年秋,我们循此线索继续追探,短短的几天里不断向南北推进,最终确认这条大路的长度接近700米,路的北端被晚期堆积打断,向南伸进新庄村,实际长度要更大。大路宽一般在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参加工作的同仁戏称其已达到现代公路四车道的标准。这一纵贯遗址中心区的大路给宫殿区布局的探索带来了曙光。
在我们钻探的过程中,有老乡告知他家地里的小麦长得不好,依田野考古的常识,这可能是因为地下有质地致密的夯土建筑基址,导致土壤结构异常所致。我遂派人去钻探,发现庄稼长势不好的地块位于著名的2号宫殿基址西北约200余米处,钻探结果又令我们大喜过望。阻碍地下水下渗的遗迹不是夯土建筑,而是坚实的路土。顺藤摸瓜地追探,居然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向东延伸,与宫殿区东侧的南北向大路垂直交叉。主干道的“十字路口”找到了!最后,确认这条大路的长度达300余米。
在探寻中心区道路网的同时,我们对宫殿区东部的大型宫殿基址群做了大规模的揭露。发掘确认在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宫殿区东部分布着一组数座南北排列的大型建筑基址,2号宫殿基址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建筑遗存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布局上相当讲究章法。这组建筑基址的下面,还分布着若干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的大规模宫殿建筑,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
就在这批宫殿基址发掘的过程中,我开始考虑下一个探寻目标——宫殿区的防御设施。我认为:具有权力中心功能的中国早期城市,其外围城垣的有无在东周时期以前尚未形成定制,但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却不应是开放的。因此我相信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应该有防御设施存在。而就目前的线索看,我们当时正在做工作的宫殿区东部的2号宫殿一带最有可能搞清防御设施的有无这一问题。如宫殿区围以垣墙,那2号宫殿基址的东墙有可能就是宫城城墙。
2003年初,我向有关部门立下“军令状”:通过最小限度的发掘,确认防御设施的有无。在二里头遗址这样延续数百年且遭后世严重破坏的大聚落上,钻探仅能提供些微线索,而无法解决全部问题。鉴于二里头遗址发掘40余年来的多次钻探中均未发现宫城城垣的线索,我推测即使宫城城垣存在,其夯筑质量和保存状况肯定较1、2号宫殿基址差,以致难以辨识。对2号宫殿基址东墙是否即为宫城东墙的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先揭开2号基址东北角,看看两米宽的东墙夯土是否继续向北延伸。
2003年春季,发掘工作按这一思路开始实施。在新开的探方中……
原文/图片出自:文明杂志社
固定链接 | 归类:精彩网摘 | 发布于:2006-02-21 13:46:41
上一页:[ 搜索引擎 ] 网站快速让Google收录的最佳方法